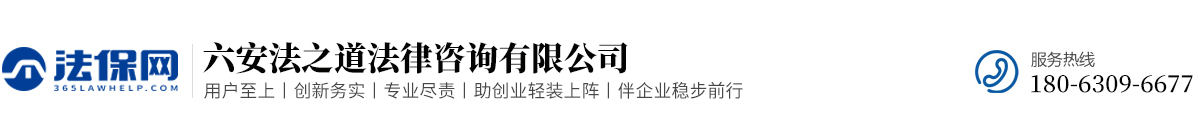徽商案例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腐敗問題的重拳出擊,全國各地查處職務(wù)犯罪領(lǐng)域案件數(shù)量居高不下。但在職務(wù)犯罪領(lǐng)域一個常見且有較大爭議的問題,就是犯罪嫌疑人的“歸案經(jīng)過”,即辦案機關(guān)采取的是電話通知到案或相關(guān)辦案人員現(xiàn)場帶離犯罪嫌疑人,“歸案經(jīng)過”的核心問題是“自首”情節(jié)的認定與否,而自首又是我國刑法法定的從輕、減輕處罰情節(jié)。實踐中,對于電話通知到案,嫌疑人主動供述犯罪事實,司法機關(guān)一般都能認定自首,但對于沒有電話通知到案的現(xiàn)場帶離行為,即便隨后嫌疑人如實供述了自身的犯罪行為,能否認定自首,存在著不同意見,且大部分意見認為不應(yīng)當(dāng)認定為自首。筆者下文重點闡述對于職務(wù)犯罪中現(xiàn)場帶離行為是否應(yīng)認定自首情形分析。
案情簡介:
筆者在近期辦理的某地原廳級干部涉嫌受賄案中,就出現(xiàn)了犯罪嫌疑人在出差過程中被紀委工作人員現(xiàn)場帶離情形,嫌疑人在被紀委部門帶離后能夠如實供述自身犯罪事實。但該案辦理過程中,紀委部門、檢察機關(guān)均未認定犯罪嫌疑人被現(xiàn)場帶離后如實供述罪行的情形屬于自首情節(jié)。而筆者在擔(dān)任辯護人后,經(jīng)過綜合分析,認為該案應(yīng)當(dāng)認定自首。
一、自首的定義。
我國《刑法》規(guī)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guān)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在我國,自首主要分為一般自首和特殊自首,一般自首要求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投案之前,出于自己的意志,向有關(guān)機關(guān)或個人承認自己實施了犯罪,并自愿將自己置于有關(guān)機關(guān)或個人的控制之下。特殊自首則要求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guān)尚未掌握的與司法機關(guān)已掌握或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于不同種類的犯罪行為。自首需要滿足兩個重要條件,主動投案以及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具體到本案中,嫌疑人因涉嫌違紀或可能的犯罪在被紀委帶離之后,積極快速如實的交代了其犯罪事實,滿足了如實供述的條件,但在是否構(gòu)成主動投案的問題上,相關(guān)單位與筆者存在分歧,分歧的焦點在于被紀委或檢察機關(guān)帶離現(xiàn)場后交代犯罪事實,是否構(gòu)成主動投案。
筆者認為,盡管嫌疑人在紀委調(diào)查其違反黨規(guī)黨紀的行為時被帶離現(xiàn)場,但并未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而且紀委將被告人帶離現(xiàn)場的目的是查明被告人是否存在違反黨規(guī)黨紀的行為,并非系檢察機關(guān)履行國家追訴職能調(diào)查搜集被告人的犯罪證據(jù)。被紀委帶離現(xiàn)場不能否定被告人被追究違紀行為時主動交代罪行的事實。
二、非人身危險性情形下的現(xiàn)場帶離不能認為已經(jīng)采取強制措施。
犯罪線索被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發(fā)現(xiàn),不能認定為司法機關(guān)發(fā)現(xiàn)、掌握犯罪事實,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雖然使嫌疑人在交代違規(guī)違紀行為期間限定嫌疑人不得離開指定地點,其人身自由受到相對限制,但與強制措施有很大的區(qū)別,并且,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將嫌疑人帶離現(xiàn)場,要求其交代違規(guī)違紀事實時,并未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畢竟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不是司法機關(guān),即使在接到舉報或發(fā)現(xiàn)嫌疑人員違規(guī)違紀的事實后,責(zé)令其在規(guī)定時間、規(guī)定地點或者直接到現(xiàn)場將其帶離,讓其交代自身的違規(guī)違紀事實,這是一種黨內(nèi)部的紀律措施,不能將黨的違紀處理措施與法律的強制措施相等同。
職務(wù)犯罪中紀委監(jiān)察機關(guān)將違紀人員帶離現(xiàn)場,應(yīng)該視作紀委監(jiān)察機關(guān)根據(jù)調(diào)查違紀行為的需要作出的即時應(yīng)對措施,只能說明紀委監(jiān)察機關(guān)對于違紀人員交代違紀事實的時間有所縮減,對違紀人員的交代違紀行為前的自由活動空間進行了限制,不能因此認為紀委監(jiān)察機關(guān)帶離現(xiàn)場的措施系刑事訴訟法中的強制措施。
三、現(xiàn)場帶離的方式是否導(dǎo)致犯罪嫌疑人喪失自首的權(quán)利
自首包含的自動投案所反映出的心理狀態(tài)和行為狀態(tài)是一種自愿性和主動性,本案嫌疑人在被雙規(guī)后,積極反映相關(guān)問題,正是其悔罪和希望獲得寬大處理的主觀心理表現(xiàn),也在客觀上減少了司法資源的浪費。從自首的立法本意和價值上說,自首制度是為了鼓勵犯罪人認罪悔罪,及時歸案,如實供述罪行,減少司法成本,更是為了教育和導(dǎo)向犯罪人,讓其可以預(yù)期到自首對其行為的法律評價。被告人是在被雙規(guī)后,經(jīng)過紀委的教育盤問,主動交代了犯罪行為。本案中,根據(jù)紀委出具的《歸案經(jīng)過》顯示:嫌疑人在調(diào)查期間態(tài)度較好,主動交代了調(diào)查組未掌握的其收受某某等人財物的事實。筆者認為,嫌疑人在雙規(guī)期間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認定為自首。第一,雙規(guī)時,司法機關(guān)并未對本案被告人進行刑事立案,雙規(guī)不是刑事強制措施;第二,嫌疑人在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的控制下,主動交代犯罪事實,符合自動投案的要件,第三,雙規(guī)期間并非司法機關(guān)采取強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期間,主動供述的行為體現(xiàn)了自動歸案的主動性。根據(jù)《最高法院關(guān)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一條規(guī)定,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guān)發(fā)覺,或者雖被發(fā)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guān)、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單位、城鄉(xiāng)基層組織或者其他有關(guān)負責(zé)人員投案的。本案中,在司法機關(guān)采取強制措施之前,嫌疑人向除司法機關(guān)外的其他單位或者負責(zé)人主動投案的,完全可以認定為自首。因而,本案嫌疑人,在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帶離現(xiàn)場后并主動供述犯罪事實,與向所在單位、基層組織等投案沒有太大差別。若這種投案供述犯罪事實的行為都不能被認定為自首,則可能將司法機關(guān)的辦案自主權(quán)急劇擴大到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查處黨員違規(guī)違紀行為的階段,混淆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與司法機關(guān)的職能范圍,不利于司法機關(guān)保持獨立、公正司法。
四、帶離現(xiàn)場后如實交代犯罪事實被認定為自首,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積極認罪悔罪。
被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約談而主動交代犯罪事實與被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帶離現(xiàn)場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并沒有實質(zhì)性的差異,二者的區(qū)別在于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對于違紀人員交代違法違紀事實的時間容忍程度。若一概將被約談而交代犯罪事實認定為自首,而否定被帶離現(xiàn)場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構(gòu)成自首,則會嚴重打擊違紀人員交代違法違紀事實的積極性,增加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調(diào)查違紀人員違法行為的工作成本,也不利于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及時將違紀人員的犯罪事實告知司法機關(guān),幫助司法機關(guān)推動司法程序的進程。由于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并非司法機關(guān),其采取的帶離現(xiàn)場的措施也并非強制措施,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向司法機關(guān)提供違紀人員犯罪線索的行為類似于舉報犯罪的行為,不能把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與司法機關(guān)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銜接認定為紀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享有司法權(quán)。并且不能因為有關(guān)線索被紀委掌握就排除自首的認定,紀委掌握的線索因為沒有轉(zhuǎn)化為證據(jù)或確定的事實,線索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此才需要嫌疑人配合進一步核實確認,而嫌疑人也是積極配合了調(diào)查,如實的反映了自己的問題,并最終確移送司法機關(guān)辦理,況且本案嫌疑人并不知道紀委是否掌握線索,紀委也沒有告知嫌疑人,已經(jīng)掌握了某某的線索。若將帶離現(xiàn)場認定為已經(jīng)對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其在紀委監(jiān)察機關(guān)主動交代的事實不構(gòu)成自首,則會嚴重損害嫌疑人的實體權(quán)益,不利于嫌疑人積極認罪悔罪,相反,被紀委監(jiān)察機關(guān)帶離現(xiàn)場的情節(jié)如對認定自首沒有實質(zhì)性影響,將會成為嫌疑人主動認罪悔罪的動力。另外,在司法實踐中,確實經(jīng)常出現(xiàn)紀委辦案采取電話通知接受調(diào)查與現(xiàn)場帶離的不同方式,而此種不同方式的標準,在《中國共產(chǎn)黨紀律檢查機關(guān)案件檢查工作條例》中也未明確,采取方式標準的不同,會導(dǎo)致嫌疑人歸案后關(guān)于自首情形認定標準的不同,進一步也會影響量刑處罰的幅度,除了可能會對嫌疑人所造成的實質(zhì)處罰不公外,還有可能賦予紀委或檢察機關(guān)過大辦案隨意性,不利于司法公正,不利于引導(dǎo)嫌疑人徹底認罪悔罪(注:嫌疑人可能因為相關(guān)人員承諾的認定自首,如實供述后發(fā)現(xiàn)自首無法認定而出現(xiàn)的心理波動和翻供情形。)
綜上,筆者認為對于職務(wù)犯罪中嫌疑人被紀委或檢察機關(guān)人員現(xiàn)場帶離并如實供述的行為評價應(yīng)以自首論為宜。有利于讓嫌疑人能夠獲得積極交代自身犯罪問題獲得自首情節(jié)的預(yù)期,在客觀上節(jié)省大量司法資源,有利于各地法院對此種情形下認定自首標準趨于統(tǒng)一,另外也從司法實踐層面解決了犯罪后先逃跑后投案認定自首的尷尬狀態(tài)。
作者:姚煒耀